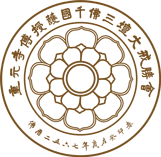{{year}}
内容提要:佛教进入中国,很快开始中国化历程。其中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的是禅宗的产生和流行。禅宗作为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中国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景德传灯录》是北宋时期的禅宗文献,它反映的是禅宗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脉络。《景德传灯录》的钦定入藏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很重要表现,也是中国政教关系的体现;《景德传灯录》编撰的主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宗法制的体现,也是佛教脱离印度佛教典籍走向自主的重要标志。
《景德传登录》是中国禅宗最早的一部灯录,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在《景德传登录》影响下,禅宗先后又出现了四部灯录,即北宋临济宗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云门宗惟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临济宗悟明的《联灯会要》、云门宗正受的《嘉泰普灯录》,南宋的普济将这五部灯录进行修订,编为《五灯会元》,成为禅宗系统最为重要的文献。
《景德传登录》的作者是苏州的道原禅师,道原禅师是禅宗法眼宗德韶的弟子。“有东吴僧道原者,冥心禅悦,索隐空宗,披弈世之祖图,采诸方之语录,次序其源派,错综其辞句,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传灯录。”[ 杨亿:《景德传灯录序》,《大正藏》第51卷,第196页中、下。]这是同时代也是《景德传登录》的当事人杨亿的说明。虽然历史上也发生了对《景德传灯录》作者的质疑,但是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我们在另外的一部书《大中祥符法宝录》中同样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道原为《景德传灯录》的作者,此书载:“右此录者,诸祖分灯,随方化导传法徒侣,记诸善言也。谈无遣有,焕乎方便之奥枢;即色明空,寂尔灵源质妙指。纪斯法印,以示禅流。有东吴僧道原,采摭成编,诣阙献上。”[ 《大中祥符法宝录》,转引自杨曾文:道原及其《景德传灯录》,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第55页。]这部《大中祥符法宝录》也是真宗朝编撰,它与《景德传灯录》的时间差别不大,因此,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景德传灯录》是禅宗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来灯录的先河,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我们认为,对道原及其所编撰的《景德传灯录》还应该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认知,才能真正理解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因此,本文拟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作一尝试,抛砖引玉,以期更多方家对此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我们认为《景德传灯录》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佛教是来源于印度的,它是印度文化的产物,与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佛教进入中国,必须进行中国化的工作,否则就无法在中国扎根,也就不能得到发展。这个历程是非常长的,从开始的以神异为媒介,到魏晋时期的借助于玄学,最后到隋唐时期的宗派的出现,大约经历六百年的时间。宗派佛教出现之后,佛教开始进入中国佛教的发展阶段,其中两宋时期是很重要的,也是中国佛教完全压倒印度佛教的关键时期。《景德传灯录》就是在北宋真宗时期诞生的,因此,它的出现体现的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
一、《景德传灯录》与政教关系
道原编撰《景德传灯录》的目的当然是为为了佛教的发展,希望这些禅宗法师的言行能够对后来的修行者有所帮助。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使得这些言行得到广泛的传播,道原是希望运用国家的力量做这一工作,因此,道原在该书编撰完成之后,便“诣阙奉进,冀于流布。”[ 杨亿:《景德传灯录序》,《大正藏》第51卷,第196页下。]
但是,道原将《景德传灯录》献给宋真宗后,并没有达到马上流布的目的。宋真宗令杨亿等人对此书进行修订,据记载:“皇上为佛法之外护,嘉释子之勤业,载怀重慎,思致悠久,乃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诰臣杨亿、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臣李维、太常丞臣王曙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 杨亿:《景德传灯录序》,《大正藏》第51卷,第196页下。]杨亿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派他进行删定呢?这就需要回顾北宋官方对待佛教的态度问题。我们知道,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便有很多的佛教典籍被翻译出来。但由于佛教典籍的数量实在太大,不是单独的个体所能胜任的。于是从鸠摩罗什的时代开始,便有官方机构参与进来,为翻译佛教经典设立专门的机构。到隋唐时期,唐太宗也为玄奘法师设立了翻译经典的机构。到宋代的时候,虽然佛教未翻译的经典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但设立官方的翻译机构的惯性仍在。“(五年正月)上览之大说,召入京师始兴译事。二月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三藏天息灾、乌填曩国三藏施护来,召见赐紫衣,勅二师同阅梵夹。时上盛意翻译,乃诏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为三堂:中为译经,东序为润文,西序为证义。”[ 志磐:《佛祖统纪》第43卷,《大正藏》第49卷,第398页上。]这种翻译经典的机构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有定例可循。在这个机构中,有一个润文,也就是对翻译的经典进行文字润色的组织。参与这个组织的,一般是汉语水平比较高,对佛教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甚至有的就是一些高僧大德。杨亿作为仁宗朝的重要人物,就曾经是宋朝的这个译经院的润色成员之一。据记载杨亿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 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奉救编修《大中祥符法宝录》,当然杨亿能够参与这样的工作,是因为除了其文学的修养比较高外,还在于其对佛教的了解深。那么,杨亿等人是如何删定道元的《景德传灯录》的呢?“臣等昧三学之旨迷五性之方,乏临川翻译之能,懵毘邪语默之要。恭承严命,不敢牢让,窃用探索匪遑宁居,考其论譔之意,盖以真空为本,将以述曩圣入道之因,标昔人契理之说。机缘交激,若拄于箭锋;智藏发光,旁资于鞭影。诱道后学,敷畅玄猷。而捃摭之来,征引所出,糟粕多在,油素可寻。其有大士示徒,以一音而开演,含灵耸听,乃千圣之证明,属概举之是资,取少分而斯可。若乃别加润色,失其指归。既非华竺之殊言,颇近错雕之伤宝,如此之类悉仍其旧。况又事资纪实,必由于善叙。言以行远,非可以无文。其有标录事缘,缕详轨迹,或辞条之纷纠,或言筌之猥俗,并从刊削,俾之纶贯。至有儒臣居士之问答,爵位姓氏之着明,校岁历以愆殊,约史籍而差谬,咸用删去,以资传信。自非启投针之玄趣,驰激电之迅机,开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传灯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应之征符,专叙参游之辙迹,此已标于僧史,亦奚取于禅诠?聊存世系之名,庶纪师承之自然而旧录所载,或掇粗而遗精,别集具存。当寻文而补阙,率加采撷,爰从附益。逮于序论之作,或非古德之文,问厕编联徒增楦酿,亦用简别多所屏去。汔兹周岁方遂终篇。”[ 杨亿:《景德传灯录序》,《大正藏》第51卷,第196页下~197页上。]从这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亿等人是如何修订的。首先,是文字方面的修订。主要是删减,就是对那些文字比较粗疏、事实不清楚、存在明显的错漏的内容一概删除。其次,突出灯录的宗旨,与之不适合,就删,需要增加的就增加。再次,对其中的序论大都删除。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杨亿等人所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但问题在于这部《景德传灯录》是道原所编撰,而杨亿等人为何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修改、道原却只能服从呢?这是因为,道原需要得到官方的认同,需要借助官方的力量,并且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就是藏经的流通必须经过官方的认同。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的体现,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佛教在印度是众多的宗教教派之一,它并没有什么政教关系的问题。但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则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很早就摆脱了宗教的影响,走向了人文主义的道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与中国社会的不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因此,人们对于佛教并不认同,佛教只是一些外来的西域商人的信仰。佛教要在中国发生影响就必须扎根于中国大地,也就是说,佛教必须进行中国化。这种中国化在开始并不明确,只是简单地生存的需要。从初期的神异佛教,到后期的玄学化的佛教,再到隋唐时期的宗派佛教,佛教是一步步地与中国社会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如何处理其余政权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要与政权发生关系,前提在于其力量的壮大。因此,直到魏晋时期,佛教才与政权发生直接的对撞。这个事件就是东晋高僧慧远与桓玄之间的冲突。桓玄作为东晋时期的权臣,对于佛教的扩张是不满意的,同时理所当然的认为政权应该将其纳入管理的范围。因此,下令处理佛教问题。当然,桓玄等人的处理方案和方式是从自身的角度进行的。但是,佛教毕竟不同于以往中国社会的力量,它是从印度传来的以出世为特征的社会力量。作为这种力量的代表的慧远自然不同意桓玄等人的观点,认为佛教不应该被纳入政权的管理范围,应该厘定二者之间的界限。经过反复的斗争,最终慧远为佛教的生存争取了空间,但政权也将自身的触角深入到佛教内部。后来,政权直接设立官员,专门管理佛教,并且在佛教内部任命官员,作为政权管理佛教的一种象征。到梁武帝时期,则更为明显。梁武帝本人在登上皇帝的位置之后,信仰了佛教,并且要以信佛皇帝的身份直接干预佛教的发展。他要亲自担任僧正,这就是白衣僧正的问题。试想一名僧界的僧正如何能够与身为皇帝的僧正抗衡,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权力对佛教的干涉。从表面上看,梁武帝作为一位佛教徒,他是要受到佛教的戒律等佛教规定的制约的,但是,以中国的传统,佛教界怎么可能制约一位皇帝呢!所以,虽然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但每一次都是被大臣们赎回。这种类似儿戏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佛教的挑战。到了隋唐时期,虽然仍然有大臣甚至皇帝信仰佛教,但其信仰从来不可能跨过世俗政权。如隋炀帝虽然拜智者大师为师,但在处理佛教问题上从来都是从世俗政权的角度进行的。唐太宗对于玄奘法师非常欣赏,但这种欣赏却是希望玄奘法师能够还俗。并且就是在太宗时期,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冲突不断,最后的结果是政权取得了最终的裁决权。二者之间的地位的高低和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世俗的统治者,这是对于宗教的赤裸裸的压制。到宋代,除了这种传统的制约外,还出现一种新的现象。宋代经济很发达,印刷业业发展起来了,佛教经典的大规模的印制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佛教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种印刷的大藏经,这就是宋代开宝年间印制的大藏经。印刷时代的来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就是文化书籍的大规模出现成为可能,因为这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同时,也会极大地影响政权的决策。书籍本身就是舆论的体现,作为政权必然不可能放弃对舆论的掌控。对于佛教也是一样。在印刷时代之前,所有的佛教经典都是手写本,这当然限制了佛教经典的流传。但是,一旦可以印刷,就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那些经典是需要印制的。在这之前,经典的流传住依靠的是个体的兴趣和爱好。因此,虽然社会上也流传着很多的佛教经典,但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控制经典的传播。即使是政府要控制其流传也代价极大,最终的结果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但是,到了这个时代,使得政府的控制的成本下降,对于舆论的压制和控制成为政权的自然选择。对于佛教来说,那些经典可以印刷流传就成为一个问题。本来,对于佛教来说,经典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来自印度的经律论和一些佛教大师的论述。经律论比较容易处理,但是佛教大师的论述则容易出现争议。谁是大师,哪一部著述是经典,这都是存在着争议的。有争议本来并不可拍,各干各的就可以了。问题在于政权并不放弃这一部分的话语权。同时,佛教本身也需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于是,政治的力量就介入到佛教大藏经的编撰中。这种介入当然是要贯穿政权的意志。换句话说,佛教的经典是否能够流通,要取决于政权的取舍。宋仁宗命令杨亿等人进行删定,就是这种政权力量的体现,道原承认这种删定,就是对这种政教关系的默认。
二、《景德传灯录》与宗法关系
宗法制是从西周就确定的一种社会关系,由于其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很契合,因此,宗法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必须与之相适应,否则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作为佛教,宗法制当然不是它的特征,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佛教是反对宗法制的。对于任何一个佛教徒来说,他们都是佛的弟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世俗的意义的。因此,这样的一种社会组织进入中国,必须进行改变,否则就会受到压制。这种改变一直在进行,中国佛教宗派的诞生,实际上就是这种适应宗法制的体现。中国佛教宗派的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必须有自己的祖师,也就是这一宗派的开创者。其次,必须拥有自己的寺院,这是佛教宗派生存的重要硬件。再次,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华严宗还是天台宗以及禅宗等都是如此。《景德传灯录》是禅宗的灯录,反映的是禅宗方面的内容。由于禅宗本身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最突出的代表,因此,反映禅宗的《景德传灯录》必然也体现其中国化的特征,特别是宗法社会的特征体现得最为明显。
第一,道统的确定。
道统的确定如同儒家明确自己的祖宗是一样意义的。对于任何家族来说,确定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祖宗是谁,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增强家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印度佛教一贯是依法不依人,认为佛教的理论比佛教的信徒更为重要。即使确定一个祖宗那也只能是释迦牟尼,不可能是任何一位菩萨和佛。但是,进入中国之后,则不同。释迦牟尼佛或者其他的菩萨只能是遥远的过去,人们需要的是现在的信仰的对象。况且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还是保留着印度佛教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哲学的意味,其神的色彩无法与后来的佛教比较。只有到了隋唐时期,佛教的中国化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宗派佛教的出现,就要求确定本宗的道统,也就是祖师序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华严宗还是天台宗,它们都有自己的祖师系统。虽然这个系统无一例外都会追溯到印度佛教中,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本土的祖师。禅宗在这一方面则更为突出,因为禅宗有一个南宗与北宗的问题。具体而言,禅宗道统的确定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禅宗与其他宗派的分际。我们知道禅宗在达摩等早期阶段是受到其他佛教势力的压制的,直到隋唐时期禅宗还是依附于其他的佛教寺院,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寺院。但随着禅宗的发展,其必然要提出自己的祖师系统,以区别于其他佛教宗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禅宗的典籍中看得很清楚。如唐僧净觉编撰的《楞伽师资血脉记》就是以楞伽经的传承来表明禅宗的谱系;唐僧杜胐所撰的《传法宝记》就是记录的北宗的谱系;唐代的《历代法宝记》则是四川禅宗保唐系的谱系;唐智炬所撰的《宝林传》则是禅宗南宗一系的谱系,此外还有一些著述也是关于禅宗谱系的。所有的这些著述的目的当然是要告诉人们禅宗的祖师系统,不过是各个派别都是有自己的私心而已。这样的一种方式很明显是起到了一破一立两方面的作用,所谓破就是排除了其他宗派的祖师在禅宗中的地位。所谓立就是树立了自家祖师的地位。这样一来就能够很好地将禅宗与其他的佛教宗派区别开来。这样的祖师系统与当时的一般家族的谱系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显然是一致的,这自然是禅宗的中国化的体现。
其次,《景德传灯录》是对自家宗旨的确定,也就是说树立禅宗南宗的地位。对于禅宗来说,基本上是认同从达摩一直到五祖弘忍的地位的,但是六祖的位置是谁则有不同。从其他佛教宗派观点来说,禅宗的六祖是谁不重要的,他们是一个系统的。但是,从禅宗内部来说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关系到自己信奉的地位问题,背后还隐藏着很大的利益。因此,必然争夺六祖的地位。从禅宗的发展来说,早期还是北宗占上风的,也就是神秀一系是正统的,对外是代表禅宗的形象的。后来北宗一系人才凋零,同时由于战乱,给了神会等人以机会,于是神会等人才公开挑战北宗的地位。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慧能所代表的南宗确实更为简单,更适应中国社会的状况,也更为彻底,因此,能够吸引众多的信众,因此,最终南宗代表了禅宗。《景德传灯录》的立场很明显是南宗的系统,因为它的祖师系统是将慧能作为六祖的。当然,道原本人是法眼宗德韶的弟子,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法眼宗的立场,故而此书中法眼宗的人数最多,谱系更完整和详细。虽然法眼宗是南宗之后最晚出现的一个宗派,但是从记录来看似乎法眼宗是最重要和影响力最大的宗派,这自然是道原的宗法立场在起作用。
第二,寺院经济的确定。
经济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组织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生存的基础。对于佛教来说,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我们知道,佛教在印度是不存在经济问题的。印度的佛教主要是依靠各类信众的施舍而发展的。进入中国之后,开始依然如此。但是,很快佛教就发现了中国与印度的不同。于是发展自己的寺院经济就成为必然。在南北朝时期,寺院便利用各种手段占有大量土地,依靠收取地租来维持和发展自己。由于势力发展的实在太快和太大,导致政府的注意,甚至引起了对佛教的压制和对寺院经济的剥夺。到隋唐时期,实行的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僧人和普通人一样可以拥有土地,这样的制度对于寺院经济的维护自然很有利。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财富是土地,因此,皇家的赏赐和大臣的捐献,往往是以土地也就是地租的所有权形式进行。这样一来,一些僧人和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就成为可能。隋唐时期,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开始形成,宗派形成的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就是要拥有自己的寺院财产。寺院的财产是依附于寺院的,而寺院则与僧人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僧人直接决定了寺院经济的归属。一旦涉及到财产问题,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也是不可能妥协的问题。但是,从理论上讲,天下的所有僧尼都是一家人,寺院的经济应该所有的僧人的。寺院不是都有挂单制度吗?这就是寺院经济共有的体现。事实上,当然财产是有所有权的,任何一位僧人和寺院都不可能将其让渡出去。因此,作为一个佛教宗派,必然有自己的寺院财产。这样的寺院财产是与宗派联系在一起的,禅宗也不例外。不过,禅宗有自己的特点。禅宗从达摩以来,几乎都没有自己固定的寺院,直到四祖道信才在黄梅有了自己的寺院和寺产。同时,禅宗的势力很单薄,以至于不得不依托其他的寺院,如《大宋僧史略》载:“达磨之道既行,机锋相遘者唱和。然其所化之众,唯随寺别院而居,且无异制。道信禅师住东林寺、能禅师住广果寺、谈禅师住白马寺,皆一例律仪。唯参学者或行杜多,粪扫五纳衣为异耳。”[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一,《大正藏》第54卷第240页上。]直到百丈怀海时才设立规矩,建立自己的寺院和管理体制。另外,禅僧基本上是在山区活动,都市中的禅僧的数量比较少。但安史之乱后,南宗的势力开始崛起,在都市中也拥有寺院。特别是武宗灭佛的发生,极大抑制了其他佛教宗派的发展,相反禅宗却得到了很好的机会。这样一来,禅宗所属的寺院和寺院经济必然扩大。于是,如何分配这些资产就成为一个问题。显然,因宗而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宗则是依靠人的。因此,对于禅宗的寺产财产而言,应该是僧人——寺院——财产,其中僧人最为重要,僧人的地位不能是任意变化的,必须具有稳定性,这样才能保证寺院的稳定性。《景德传灯录》的出现,事实上也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景德传灯录》的内容很多,但脉络还是很清楚的,它是按照宗派的属性撰写的。通过阅读《景德传灯录》就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当时僧人的归属。这种归属是宗派的归属,确定了宗派,自然也是确定了宗法,当然也就确定了寺院财产的归属。
第三,师徒制的确立。
宗法制中的人际关系最基础的父子关系,对于佛教僧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师徒关系。但是,传统的佛教僧团是不存在严格的师徒关系,彼此之间是平等,大家都是佛弟子而已。寺院经济的出现,使得佛教僧团不得不明确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寺院的归属关系,否则,就会出现混乱。佛教宗派出现以后,这个问题自然就转化为师徒关系。对于禅宗的宗派来说,一座寺院和其所附属的财产是与寺院的创立者密切相关。人们依附于这所寺院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寺院的创立者的依附。作为寺院的创立者自然是将其所创立的寺院作为自家的宝贝,同时对自己的修行法门也是信心满满,否则其就没有必要独立门户。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保证自己的教法能够延续下去就是其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教法并遵从的自然是自家人,这当然就是自己的徒弟。一旦创始人去世,自然是其弟子继承这座寺院和寺院所属的一切。很明显,这样的寺院就是后世所说的子孙丛林。而所谓的四方丛林不是没有,但是数量是比较少的。即使有所谓的四方丛林,外来的住持也很难控制寺院的寺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寺院的住持不过是过客而已,真正掌控寺院的还是与寺院有着密切关系的原来的僧人,而这些僧人无一例外都是原来的寺院创立者有着宗法上的关系。所以师徒制度一方面是保证寺院的修学特色,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保证了寺院的所有权能够始终控制在自家人手中。因为经济是基础,只有经济实力控制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保证寺院的修学方式的方向按照原有的轨道进行。当然,这样的安排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但无论如何都是内部的问题,不会让外人介入。《景德传灯录》通过书面的方式,将各个宗派的继承和源流一一记录下来,这就为可能出现的纷争确定了一条标准。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座寺院是哪个宗派的寺院,其历史的传承是怎样的,都是非常清晰的。
以上,我们简单地从寺院的道统、寺院经济和传承三个方面探讨了《景德传灯录》与宗法制的关系。当然,《景德传灯录》的作者道原法师未必有这样明确的意识。但是,一部著述之所以这样安排而非那样安排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未必是其真正的目的,但原因背后的背景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道原虽然未必有意识按照宗法制的宗旨撰写《景德传灯录》,但《景德传灯录》却体现了当时禅宗这个宗派与封建社会宗法制的关系。
三、《景德传灯录》与禅宗的修学方式
作为从印度传来的宗教,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其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与佛教的禅定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人们一谈到禅宗,自然地将其与禅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禅定作为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是各派共同的,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禅定而禅定,是为了信仰佛教,真正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我们经常说佛教一言以蔽之就是了生死,也就是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当然这种解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决,而是指人们真正能够看透生死。所以,佛教所有的一切都是服从于这一目的的,佛教的修行方式自然也是要服从于此。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修行方式最早还是以禅定为主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早期中国的一些佛教大师的经历看得出来。后来,中国佛教宗派兴起,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独特的修行方式。在这些修行方式中,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以义理为特征的,如天台、华严等;一种是实践性比较强的,比如禅宗和净土。
禅宗与其他宗派最大区别就是修行方式的不同。禅宗的修行方式是从达摩的时代就确定了的。达摩作为禅宗各派都认同的祖师,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理论上坚持“心性本净,客尘所覆”,因此要去尘,回归本心;在修行的方式上坚持壁观。无论是理论还是修行方式,都与其他宗派形成鲜明的对比。达摩的这套系统一直被继承下来,直到神秀慧能的时代才发生分裂。前者形成禅宗的北宗,后者被称之为南宗。前者主张渐悟,后者主张顿悟。后来慧能所代表的南宗占了上风,成为禅宗的代表。对于禅宗来说,其典型的表述“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等,这些表述尽管是不完全的,但基本上还是将禅宗的家风体现出来了。南宗禅最终能够取代北宗禅,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其修行的理念和方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更具有中国化的特点。而《景德传灯录》作为一部记录禅宗源流和发展历史的著述,自然也体现出其中国化的方方面面。
第一,“传灯”与禅宗特色。
所谓灯,就是我们照明用的灯。灯只有在黑暗的场合才有作用和意义,灯的作用一是破暗,二是指示道路。从破暗的的作用来说,就是道原所撰写的禅宗的历史是破暗的历史。也就是说,禅宗对世俗社会的基本判断与佛的教导是一致的。我们所处的世俗社会是一个染污的社会,是需要拯救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不值得追求的社会。如果没有佛教的道理出现,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一直黑暗下去。佛的教导来了,就是黑夜里明灯,于是人们才能发现自己周遭的黑暗和不如意,才能升起对光明的追逐的心。有了对世俗社会的正确认识,才能够进入寻找光明的境界,这个寻路的过程就是各家各派的宗旨的问题。对于禅宗来说,就是禅宗的宗旨是引导众生走向光明的唯一方式。禅宗祖师的一言一行就是引导众生的明灯,他们的延续不断就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也就是传灯的过程。因此,《景德传灯录》所要表明的是各位高僧大德的追逐光明的心路历程,通过将这些心路历程记录下来,就可以让后来者少走弯路,尽快提升境界,最终达到解脱的境地。
第二,《景德传灯录》的内容取舍特点。
在《景德传灯录》之前,中国佛教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佛教祖师的传记。如南朝梁时的慧皎就编写了《高僧传》,唐时的道宣撰《续高僧传》等,即使是禅宗之前也有一些典籍出现。但是,《景德传灯录》与之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景德传灯录》不是简单地记录某个僧人的事迹,而是将其具有代表性的言行记录下来,通过简单的言行就将其精神实质体现出来了。《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内容很多,记载的人物也有近二千人,但其中所围绕的问题却不多,基本上集中在下列问题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意与教意是否一致?祖师之间代代相处的道德是什么?三宝是什么?法身是什么?如何是佛?如何是祖等等问题。从形式上看,这些问题似乎都是佛教的根本问题,需要对佛教理论有非常高深的理解才能回答。但是对于禅宗来说,根本不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书中所记载的并不是历代先贤对这些问题的理论上的回答,而是通过特定的语言和行动来打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进而能够明确自己思维的误区,从而得到不断的提升,并最终得到解脱。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真的问题,它们只是一个引子,通过这些引子才能进入真正的解脱之路。道原的这种取舍应该说是把握了禅宗的精神实质。对于禅宗来说,其特长显然不在精致的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要服从最终的解脱的,它们只不过解脱之路上的一个工具而已。如果执着于这些理论,就会丧失本心,忘掉初衷。因此,禅宗教人才是教外别传,它要通过各种手段打破人们对佛教的迷思,进而直指人心,这样的方式才是顿悟。应该说,禅宗的这套宗旨相对于其他的宗派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具有中国的特色,也最能与中国文化相契合。中国文化中最典型的是儒家,儒家思想相信人都有本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不过平时的良心都被遮蔽了,因此只要认真修行,就会将这些遮蔽去掉,显示良心的本来面目。禅宗的方式显然与之最契合。因此,人们才会说禅宗是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第三,《景德传灯录》与士大夫的需要。
宋代对待文官的态度比任何一个朝代都优待,文官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高。文官主要是通过科举选拔的,科举的内容自然是儒家的思想为主。这样的文官决定了他们对佛教态度,而文官又把持了国家机器。因此,佛教要发展,自然也不开与文官打交道。因此,取得国家文官系统的好感对于佛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取得他们的好感呢?很明显,过去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了。隋唐时期,儒学凋零,社会上的真正的大学问家和大师基本上都是佛学大师,佛学大师依靠他们对佛学的学问就足以获得社会的赞誉。但是,宋代的社会风气已经完全不同,作为人生的出路,读书人基本上都是要靠科举的,他们不可能将精力用在佛教理论的学习上。我们都知道佛学是博大精深,即使是中国化的天台宗、华严宗也不是容易了解的。这就决定了依靠义学很难获得士大夫阶层的好感。禅宗的不立文字的特点这个时候就可以派上了用场。《景德传灯录》中所记录的法师们的言行实在是精彩,也特别适合对佛教有兴趣,但又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士大夫。书中的语录并不是真的佛教理论,而是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法师们的一个动作也具有神秘的意义,这些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自然是有吸引力的,也是适合他们的佛学水平的。对于士大夫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真正了解佛教的高深理论,他只需要一知半解就可以了,因为佛教只是他们生活的调济。《景德传灯录》中所记载的法师的言行确实能够将士大夫从日常的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给他们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只有这样,士大夫才能对佛教产生兴趣,佛教也才能从士大夫阶层那里得到助力,从而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记载中看出,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的佛学修养水平明显没有隋唐时代的高,而且士大夫与僧人的交往只是生活情趣方面,对于佛教的高深理论很少涉及。可以说《景德传灯录》是在无意中契合了时代的需求,从而保持了佛教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为佛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护。
总之,宋代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发展阶段,佛教也从精致的理论建构走向民间的流传。重新建立佛教与士大夫阶层的良好关系就成为迫切的任务,《景德传灯录》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这种回应既是中国禅宗宗旨的延续,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体现。
王公伟,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授。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红旗中路186号
E-mail:wanggongwei@163.com
苏州工业园区重元寺出品
▍版权声明:
○ 本文部分文字为网络采集,由苏州重元寺编校发布,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
○ 版权归创作人所有,我们尊重著作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如涉及版权争议,请著作权人告知我方删除,谢谢。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苏(2022)05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