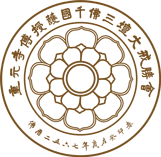{{year}}
摘要:《景德传灯录》之编撰去唐未远,映射出盛唐佛教中国化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华传统历史编纂学卓著的创造性成果。因此,它不但在中国禅宗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至今不失其历史编纂学的体裁价值。学者在以《景德传灯录》为代表的灯录体史书之外,发掘更丰富多样的史料值得赞赏,但因之否定《景德传灯录》作为禅史学基本史料的地位则有失公允。从中、印文化交相辉映的视角看,《景德传灯录》更有其重要价值。继胡适发掘敦煌史料之后,历史学者又发现不少唐宋碑刻,其记载与倾向都和灯录近似,这也证明了灯录所述的史料价值。不但如此,《景德传灯录》所载印度文明输入中国由初期难免碰撞到逐渐消化吸收的缩影,也启迪着人们该转换模仿欧美文明包括其话语系统的心态了。
关键词:中国佛教史学 中国禅宗史 中国学术思想史 中国历史编纂学 公共史学
一、《景德传灯录》之编撰与史学地位
《景德传灯录》30卷,系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禅僧道原所,道原生卒年不详,乃法眼宗天台德韶禅师法嗣,,与著名佛学家永明延寿禅师(904-975)乃同门弟子,他以佛教史学名世,居姑苏承天寺(今重元寺)永安院,想其时已垂垂老矣。他向宋真宗进呈其据《祖偈因缘》、《宝林传》等书合编的《景德传灯录》,“灯录”始以名书。“灯”取其光明义,以喻通过代代相传的明灯,给众生带来光明。名居士、大儒杨亿为该书作序称:是书“披奕世之祖图,采诸方之语录;次序其源派,错综其辞句。”又“校岁历以愆殊,约史籍而差谬,咸同删去”。“聊存(禅宗)世系之名,庶纪师承之自”。[ 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点校本《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这说明了灯录体史书在历代《高僧传》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创造,不但详记师承源流,还以相当大的篇幅,生动活泼的语言(唐宋时的口头语,与儒家史籍的文言文完全不一样)记载了禅师语录及丰富多彩的参禅方法,以供修行揣摩之用,诚全新禅学史。如今荟炙人口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枯木逢春”、“抛砖引玉”、“牛头马面”等典故均出自该书。该书共收录禅门历代祖师凡一千七百零一人事迹,附有语录者九百五十一人,史料极丰。其承袭古书的印土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事迹,虽不免被神化的印记,其实已带有印度佛学传承之史的性质,至于“祖”字的翻译运用,更鲜明地有了“祖述尧舜”的中国色彩。该书虽有对古籍故意把达摩多罗(佛陀跋陀罗译有《达摩多罗禅经》)与菩提达摩混为一谈等等失察的问题,但作为最早刊板的禅宗专门史应该加以高度肯定。
《景德传灯录》的编纂也颇有本之于佛学,同时受相对于当时世界水准而言已很发达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历史编纂学影响的法度,其首冠《西来年表》,大体依《祖偈因缘》而扩至三十五祖,正文每传先列祖师名号,然后概述其经历,摘引其机语或著作,末系一偈,总结其传法机缘。其编排则依禅宗宗派分列而系年。以故此后《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玉英集》、《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等续、扩之作不断,影响极大。南宋禅僧普济将五种灯录汇编成有名的《五灯会元》,然仅删繁就简,便于流传,在体例与内容均无大的改进。元明清续作更多,现存者达二十余种。
在《景德》、《天圣》两灯录问世之后,释契嵩撰《传法正宗记》十卷,附《正宗论》两卷,该书主旨分明在于为给南宗禅及其后传确立正统地位。作者称:“祖者乃教之大范,宗者乃其教之大统。”夫古今之学辈竞以所学相胜者,盖宗不明祖不正为其患也。“因此作者“窃欲推其宗祖,与天下学佛辈息争释疑,使百世而知其学有所统也。因以众家传记与累代长历校之修之,编成其书。”[ 契嵩:《上皇帝书》,《传法正宗记》卷首,《大正藏》第五十一册。]很明显,至宋代,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及其争嫡系的传统对佛教的浸染愈益加深,在此“宗教”一词与西方唯一神教的意味也迥然相异。该书之编纂也贯彻了这一“宗旨”,仿孔子编删《春秋》寓“褒贬” 之义也更浓,与《景德录》重心在禅学思想与修行方法的传承差别甚大。其书传记分为“天竺”、“震旦”“诸尊者传”,《正宗分家略传》、《旁出略传》、《宗证略传》四类,其称“略”是因诸祖师有行迹可记者多见于《景德》、《天圣》两录,因而略之仅叙世系。该书前冠《始祖释迦如来表》,后系《传法正宗定祖图》,所附《传法正宗论》专以阐明自达摩至南禅一家之师承,门户之见色彩浓重,由此更见《景德录》编纂思想的可贵。
灯录与《传法正宗记》的编撰思想及其体例给朱熹编最早的儒家学术思想史《伊洛渊源录》以诸多启发,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垣、顾颉刚不约而同地阐明了此点。[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页92、93,北京:中华书局196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页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伊洛渊源录》是当时儒家学者借鉴禅门灯录类史书,创造性地用以阐扬儒家正统地位的儒学史代表作。当然,朱熹编此书很明显也受到唐韩愈“儒家道统说”的启发,但孔、孟之对于儒家,其地位确相当于“西天七祖”对应于中国佛教。明代周汝登撰《圣学宗传》,有接续《伊洛渊源录》的意图。但周汝登本人亦喜参禅,受禅宗影响,其编纂思想竟类似《传法正宗记》,其体例亦如灯录,列有自远古伏羲至明代罗汝芳八十余人传略,每传后以按语代替偈语。
明大儒黄宗羲撰著名的《明儒学案》,有鉴于《圣学宗传》,但《明儒学案》中有关学术思想承传的记述极大地得到了增强,可谓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典范之作。该书各学案前多有小序,阐明立案之旨即该学者之学术思想在明代儒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名者实之宾,“学”之名,顾名思义讲学术,然而为何称“案”?仅为传后有编者按语吗?其实不然,这也是受禅宗影响之故。宋代禅门“公案”类著作已盛行,如禅僧无门慧开所撰《无门关》即著名的代表作。这类书选列祖宗师之间的问答语加以评介,作为授徒参究之用。尽管这类语录问答汇编的选材并非有意识地组织编排,但因对禅修有启发,其影响远超学术著作,儒、道为授徒需要也纷纷仿效。如元道士苗太素编《玄教大公案》,即径取“公案”为名,但其选材已相当有组织有系统,具有宗教思想史资料选评性质。明儒家学者刘云卿只改“教”为“学”,即命名其所编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至王阳明等26家语录为《诸儒学案》。黄宗羲承之,增以学者传略、会语录、传记、学脉承传三者为一,学案体的创立乃水到渠成。当然,他由深刻反思明亡教训而增长的学识,才是《明儒学案》被广泛称颂,至今续作不断的根本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声誉已无人否认,其中也包含着《景德传灯录》的创造性影响。而后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当代著名学者杨向奎编《清儒学案新编》[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85。]以及并非只收新儒家一家,而囊括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各派代表的《百年学案》,[ 杨向奎等:《百年学案》,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为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之一,可见《景德传灯录》之深远影响。惜《百年学案》中收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开创人,竟无佛学思想家之一席之地,笔者因有《当代人间佛教传灯录》之作。
二、《景德传灯录》的史料价值
全盘否定以《景德传灯录》为代表的灯录体史书的史料价值是从胡适开始的,胡适自称:“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作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呈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他还认为,禅宗大部分经典著述,包括五套《传灯录》,从《景德录》到13世纪相延不断的续录,都是编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他也知这么说不妥,因而又解释:“我这些话是说重了,但这却是我的老实话。”[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页255-257,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在此,笔者作为历史学者,有必要纠正胡适从史学出发说的过头话,也就是要重估这些史料中被“说重了”的部分,而不是象铃木大拙作为禅者、或象柳田圣山那样作为佛学家那样鸡对鸭讲。
1、胡适对现代禅宗史研究的开拓之功应肯定。他挖掘了大量新材料,这些新材料的价值也很少可非议。但新材料恰恰是在与灯录类史书的比勘中才显现其价值的,即依胡适来看,可疑的只是马祖(公元709-788年,一说688—763)以前的南宗禅谱系,灯录体史书记载的马祖以后禅师法脉承继及其生平、语录等所含的基本史料价值具存,不可从根本上否定。而仅此已远超10%了。在《景德录》中,叙马祖以后的史料乃第六卷至三十卷,占全书比例达83%以上。而续补《景德录》的各种灯录系该类史书中的多数,其所记载的更是往后的谱系及传主事迹,可靠性更强。
2、胡适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大规模地输入最早出现在欧美的现代观念的功绩也应肯定。但他把现代化与传统绝对地对立起来,由此怀疑、批判一切传统的“过分”,在今天不得不反思。在胡适的提倡下,钱玄同改名“疑古玄同”,顾颉刚提出古代“层累造史说”等等,他们固然也有不少创见,但当年被他们否定的许多古文献记载的史实却被以后的考古发现证明为真。至于胡适对禅史的考证,可以说是他为自己所提倡的实证主义亲自披挂上阵,未免勇猛过当。如他说《坛经》为神会所作已被今人否定。在当时,或许矫枉过正有其必要,非此,就不能使思想挣脱神化的束缚。但胡适本人却因此也尝到了一味反传统的苦果——在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令他最痛心的不是唱高调者,而正是其实证主义主张哺育的学生批判者。从余英时先生分析思想史的“内在理路”看,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到对各种非“主流”的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这正是激进再激进之势所必然。因此,全盘否定《景德传灯录》的史料价值的主张也可休矣。当然,在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中也应警惕另一种矫枉过正,即“翻烙饼”式而非建设性的批评并无意义。
3、以传教倾向之大体而言,唐代中期禅佛教之南北宗之分,其实主要是以面向中央朝廷,还是面向中下层社会(包括地方官吏及失意士大夫等)为别。神秀代表的北宗不可能悟到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言:“统治的官僚向来一方面是广泛的冷静的理性主义的体现者,一方面是有纪律的‘秩序’和安定理想的体现者,并把这些视为绝对的价值准则。对一切非理性宗教信仰的深刻蔑视,同时又看到它们作为驯服手段的可利用性,一般都是官僚体制的特征。”[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页536,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当然这是以官僚作为社会集团的亲缘性而言,并不否认个别官僚倾向于特定宗教。)因而终归失败。相反,南宗以深入中下层社会而成就。在历史社会学视角看来,《景德传灯录》所记载的有成就者之历史不足为怪。胡适发掘被隐去的历史也值得称道。有此两面,方构成较完整的历史,即公共史学之历史表述。至晚唐、两宋,南宗思想与教法体系已趋成熟,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佛教派别。其世次既多,支派繁衍,自必撰史为之总结。设无《景德传灯录》,不知今日之考证从何着手以恢复当年历史图景?何况即属虚构的神话和寓言,也自有当时人创作的蕴含意义。以古为神圣的时代固然应褪其记载的神化光环,今人要苛求古人也不难,但即便在中国近代,党派史与宗教史中还不是同样存在着造神现象,存在着只写一面,而抹煞另一面真相的倾向,这难道就不是胡适所称的“伪造”吗?神化古代的复古论固然误导今人,“以今律古”,而不能体谅古人用心,吸取前贤智慧也属同样性质的误导。
4、胡适主张,必须摆脱佛教徒撰写的灯录体史书固有的倾向性,客观地重建禅宗史。对此,历史学者应努力。但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纯客观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能够做到的是去“我执”而力求公允,当代史学界正在兴起的“公共史学”,即代表着多元文化对话中形成的共识。以对胡适的禅史研究评价为例,他高度肯定了禅宗的“革命”,认为从印度禅到中国禅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不断注重坐禅“修心”。从康僧会的“明心”、僧稠的“修心”和僧实的“雕心”,再到马祖的“平常心”可以看出,没有不是强调“心”的。最后由马祖的“平常心是道”得出禅的简化,而完全确立了中国禅。[ 张 军:胡适禅思想述评,http://www.fjdh.cn/wumin/2009/04/21483764892.html]当然,胡适也看到了慧能的“明心见性”在其中的关键地位。不过,胡适在文化上也是改良主义者,他异乎以往地高度评价禅宗革命,说到底还是因袭了佛教徒以印度佛教为正宗的立场,认为南宗禅是对印度禅的革命。不过,他早年的心中可能并不以“革命说”为然,赞扬一面是为了平衡另一面的贬低,以使读者接受其见解。至其晚年,胡适才吐出“老实话”即他考证禅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珍宝从中国文化的粪便中“耙”出来。[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页255-257。]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也可见他对灯录体史书的态度。其实至禅宗诞生为止,国人引进、消化、吸收印度文化起码已五百余年,因而有少数人已真实地领会到释迦牟尼的般若智。即便他们融入了老庄的睿智也正常,只有以印度佛教为正宗,才将此视作异常。当然,胡适的根本立场在于强调知性,在于主张从欧美学来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华文化的新生而言,晚清以来欧美近代文化的引进是一大契机,胡适等有大功。惟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本身,也只是欧洲对古希腊希罗多德史学的“复兴”之流变,欧美并未因其古代的许多神话传说与史实夹杂而全盘否定自身传统。就宗教学研究而言,也正是源于希伯来文化的欧美《圣经》诠释学推动了比较语言文字学、比较宗教学、宗教哲学、宗教史等学科的发展。因而,胡适以两希文化及其发展为唯一正确的知识系统来衡量中、印文化,并不很“客观”,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笔者期望后学从公共史学视角出发,整合两派乃至多派不同见解,撰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禅史。《景德传灯录》所载印度文明输入中国由初期难免碰撞到逐渐消化吸收之缩影,启迪着我们该当转换一味模仿欧美文明话语系统的心态了。
5、“平常心是道”也不仅是对禅的简化。它既是一种在外界任何刺激面前都能从容以对的极其稳定的心态,也是在摆脱了对印度传入的佛教经典的教条式理解的束缚之后,建立在对佛学原理的理性领会之上的更高的直觉洞照。这一心态面对刺激的寂然淡定,不是出于懵懂无知,也不是出于麻木,而是出于了达生命底蕴的洞照。当然,对印度传来的思辨文化与瑜伽数息术的消化吸收能达到如此程度的汉地僧俗,也是很难得的。这需要有前人长期经验的积累与传授点拨,也需要个人天资颖悟与无数次的习练。同时在技术的把握上,经久而久之练习盘坐与调息后,自然熟能生巧,于是坐的形式也可扬弃,坐卧行住皆是道。这就是马祖开启的生活禅,生活禅不但关注杂念不起,而且因悟后有面向现实的洞照,可对各种生活中的问题解决,予以启发性的指点,众人由此感到了不起而升起崇敬。但除此之外,凡圣一如,汉地高僧大德喜怒哀乐、吃饭睡觉都与常人一般无二的平常。但由于他们的人格魅力,其弟子及众人受其指点,被其感化,口碑流传,“所过皆神”,于是未免把他们神化了。《景德传灯录》等史书大都系他们的弟子或徒裔所记所编,而不符徒弟们崇敬口味的史料都被遮掩了,这就是胡适称之为“伪造”、“矫饰和装腔作势”的另一原因。还有一原因则是高僧传与灯录同具的,承接于儒家的“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但因诸灯录的编者距古不远,可以肯定,胡适在现代看到的“新材料”,大部分也被有些编者看到过,只是有意无意不录入罢了。而胡适之所以能重新变废为宝,也正因与灯录编者着眼的角度不同。因此,如果换一与胡适不同的视角,例如从中、印文化交相辉映的仰角看,《景德传灯录》则仍有其重要价值。继胡适之后,历史学者又发现不少唐宋碑刻,其记载与倾向都和灯录近似,这也证明了灯录所述的史料价值。
三、《景德传灯录》历史编纂体裁的当代价值
欧美现代理性化的知识系统,虽然肇始于古希腊之学科分类,然其真正发轫,还系结于欧洲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分别从内外两方面,打破了天主教神学意识形态对个人理性的束缚。同为轴心文化发源地,谁也不敢说无论是印度人、中国人,还是希腊人与希伯来人,在个体理性思维的能力上有多大差别。在探索、确认与构建全球共享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知识体系的进程中,近代中国与印度的贡献之所以较少,在印度主要因印度教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仍受到特权阶层的强力维护,民众思想仍被其束缚;在中国则因新文化运动虽推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但民众的头脑才挣脱儒家意识形态束缚,又被打着“西学”旗号的意识形态禁锢与愚弄。康德对所谓启蒙,作了相当深刻的概括:“启蒙就是人从其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中走出来。‘不成熟’是指缺乏在没有他人(如意识形态权威)指导下运用自己的理智的能力。如果这种不成熟的原因不是缺乏理智,而是缺乏在没有他人指导下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便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成为智慧者!’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1991, p.54 ,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页22,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这一理智能力的运用也包括对东方传统文化价值的合理评估,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传统中国科技成就的评估就相对公允,他说:事实证明,注重代数学的中国数学与注重演绎几何学的西方数学,使用赤道座标和注重天极和时间计量的中国天文学与使用黄道座标、注重行星和角度计量的西方天文学决非互相对立和不相容的,它们都一起汇人了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海洋。他还认为,某一领域的有机程度(包括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因素)越高,在中国与西方不同进展的交叉融合点就将愈晚出现。[ [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页241,沈阳: 辽宁科技出版社, 1986。]中国传统史学与欧美传统史学的有机程度都很高,其理论方法都在古代已自成知识系统,其间的主要差别在关注点往往不同,例如各自都关注本地的地方性知识。如依李约瑟的推理,双方的融合比起数学、天文学自然要晚,但随着欧美繁杂的(实证主义仅为其主流之一)现代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消化,随着语言交流障碍的突破,两者,甚至三者即印度史学也都终将汇入现代人文知识体系的海洋。
目前国际史学界与中国史学界的隔阂除了意识形态、理论方法因素不同外,主要还在于中国学者的成果如不用英语及本领域小圈子认可的形式发表的话,很难有国际反响。尽管汉语学界对欧美学者的成果了解也有类似情形,但国外成果的中译本相对更多些。
以《景德传灯录》为代表的灯录体史书是中印文化交融的结晶——禅宗创立的记录,也是随着佛教中国化的成功,本来就是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在汉地实现了本土化,独特的中国佛教史学因之确立的标志。因此,才有儒学、道家相继仿效(而不是以往佛教史著模仿儒、道)。当然,中华佛教史学依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分支,其记载对世界而言,属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系统。但史学界往往因“宗教”敏感而对其不够重视,恢复其应有地位仍需历史学者的努力。
灯录体史书中虽存在片面录存对本宗派衍传有利的史料,贬斥其他佛教宗派的门户之见,但其编撰意图包括为禅之教学而用,因而其在现代之应用仍宜于作为各界善信承继佛教或佛教文化的优良传统之教材编写,宜于作为佛学院师生结合现代人根器,把握修行方式的参考书而编撰。当然就其体裁而言,也不必再限于禅宗,为佛教各宗派在当代的宗风承继,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都可借鉴运用。事实上,在宋代不但有儒家的类似著作,也有天台宗的类似著作问世。
以《景德传灯录》为代表的灯录体历史编纂体裁也有其不可抹煞的当代价值。这一体裁,其实融欧美史著也极为重视的传主生平思想事业的评价、原典、参考文献等为一炉,既有便于全面了解、研究的传统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长处,也克服了照搬国外模式,分别出版思想史、学者传记、研究资料汇编,以致于有读者顾此失彼,出版社考虑到销量有限,往往不愿出研究资料汇编等不足。如果能吸取欧美学术思想史分析深入之长,这一史裁在当代将有更强的生命力。
苏州工业园区重元寺出品
▍版权声明:
○ 本文部分文字为网络采集,由苏州重元寺编校发布,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
○ 版权归创作人所有,我们尊重著作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如涉及版权争议,请著作权人告知我方删除,谢谢。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苏(2022)05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