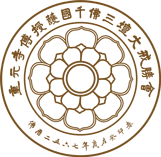{{year}}
摘要:禅宗前史之“西天二十八祖”“七佛传法偈”等记述,虽可导源于唐代《曹溪宝林传》、五代《祖堂集》诸书,而实由北宋之《景德传灯录》定型。兼之后《宝林传》《祖堂集》皆佚,20世纪初方重新现世,且《景德传灯录》有钦定性质,故影响后世禅宗者实为本书。由《传灯录》关于禅宗前史之叙事,颇可见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之思想特色,且《传灯录》中尚无“拈花微笑”之说,而出于稍后之《联灯会要》,亦可见禅宗前史建构之次第。要之,《景德传灯录》所述之禅宗前史,虽未必全为“事件的真实”,然其“意义的真实”则不容否认,其于文化认同之整合作用,自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关键词:《景德传灯录》;禅宗前史;佛教中国化
宋代道原编撰之《景德传灯录》系我国禅宗史之根本资料。集录自过去七佛,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共1701人之传灯法系,其中附有语录者951人。以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具表上进,并奉敕入藏,故以“景德”名之。——在《景德传灯录》之前,禅宗灯录的撰写,尚有唐代的《曹溪宝林传》及五代时的《祖堂集》为先驱,然《宝林传》后世几近亡佚,20世纪30年代才于赵城金藏中重新发现;《祖堂集》则于中土亡佚已久,至20世纪20年代才由日本学者于朝鲜重新发现。至于长期以来被宗门所长期奉为圭臬、且有官方钦定性质之禅史著述,仍当推《景德传灯录》为第一。
关于禅宗“前史”之佛祖付法因缘、偈语等记录,按宗门旧传,东魏静帝兴和二年(540)有高僧云启(宋契嵩《传法正宗论》作“昙启”)往印度求法,途经龟兹,遇北印三藏那连耶舍欲来华弘化,遂挽留暂住,共译《祖偈因缘传》。后耶舍东来,把《祖偈因缘传》授予居士万天懿。当时另有流行于北魏境内,传系印度三藏吉迦夜共沙门昙曜共译的《付法藏传》,序次失当,兼缺偈颂,乃以耶舍译本校正其失。梁简文帝闻有此本,遣使前往传写,因得流布南方。唐贞元间(785-804),慧炬携《祖偈因缘传》往曹溪,传说其同印度三藏胜持重加参校,并编次诸祖传法偈语及唐初以来宗师机缘,集为《曹溪宝林传》。唐光化中(898-901),华岳沙门玄伟续集贞元以来宗师机缘,编为《玄门圣胄集》(已佚)。朱梁开平四年(910),南岳沙门惟劲续集光化以来宗师机缘,编为《续宝林传》(已佚)。其后,南唐保大十年(952),泉州昭庆寺僧静、筠二师,续有《祖堂集》的编撰,体例略同,而内容记载稍有出入,又多收禅门歌行偈颂。道原编撰《景德传灯录》,对以前诸籍综合取材,并广事网罗,重加组织,为现存禅宗史中最初具有完整规模的一部。尤其对于禅宗前史(惠能以前)的叙述,亦由其最终定论,以至早年之学者若忽滑谷快天等,因未见《祖堂集》、《宝林传》等书,皆以《景德传灯录》为最早凭据。《传灯录》卷一、卷二叙述过去七佛与及西天第一祖摩诃迦叶至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之传法情形,卷三叙述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东土五祖之传法情形,皆为后世禅宗援为定论。
一、关于西天二十八祖
禅宗关于天竺祖师传承的世系,根据胡适先生的考证,当为南宗争夺正统时期开始出现的。最早有神会的八代说,后又“有二十三世说,有二十四世说,有二十五世说,又有二十八九世说。唐人所作碑传中,各说皆有,不可胜举。又有依据僧祐《出三藏记》中之萨婆多部世系而立五十一世说的,如马祖门下的惟宽即以达摩为五十一世,慧能为五十六世(见白居易《传法堂碑》)。但八代太少,五十一世又太多,故后来渐渐归到二十八代说。”[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20世纪佛学经典文库·胡适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434页。]“二十八说的前二十三代的依据是《付法藏传》。《付法藏传》即是《付法藏因缘传》(《缩刷藏经》‘藏’九)号称‘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此书的真伪,现在已不容易考了。但天台智顗在隋开皇十四年(594)讲《摩诃止观》,已有此传,历叙付法藏人,自迦叶至师子,共二十三人,加上末田地,则为二十四人。”[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20世纪佛学经典文库·胡适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435页。]而二十八代说之最后四代婆舍斯多、不如密多、般若多罗、菩提达摩则为禅宗所独有。
故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之说,早在唐代已有争议,释神清在所著《北山录》中即曾对其说加以驳斥。《景德传灯录》则系沿用《宝林传》之旧说,彼时在禅宗内部亦尚未形成共识,天台等宗更攻之颇力。后契嵩鉴于禅门传法世系的众说纷纭,并为反对天台宗依据《付法藏因缘传》所主张的西天二十四祖之说,起而著《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诸书,论证二十八祖说之合理性,以禅宗为上承佛祖的佛法正宗,并曾与天台宗山家派僧南屏梵臻及山外派僧子昉等往复辩论。嘉祐七年(1062)三月,契嵩所著三书(合称《嘉祐集》)与《辅教编》一并蒙敕编入大藏。[ 参见宋道发:《佛教史观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35-36页。]经过契嵩的论证,《景德传灯录》所主的西天二十八祖之说终于成为后世禅宗传法世系的定论,《景德传灯录》从此亦成为叙述禅宗传法源流的权威典据。
不过若从史实考据而言,不仅二十八祖说的最后四代未见出处,即使源出于《付法藏因缘传》的前二十四代,也甚为可疑。若田光烈先生指出,《付法藏传》之二十四代,“从佛灭度时以最胜法咐嘱大迦叶起,其后以次传法为阿难、摩田提、商那和修、忧波毱多、提多迦、弥遮迦、佛陀难提、佛陀蜜多、胁比丘、富那奢、马鸣、比罗、龙树、迦那提婆、罗睺罗、僧伽难提、僧伽耶舍、鸠摩罗驮、阇夜多、婆修槃陀、摩奴罗、鹤勒那、师子。其内容多取材于旧籍。象《优波毱多》传记的一部分,就是大体上采用安法钦译《阿育王传》的原文。又象《龙树提婆》传记部分,也是用罗什所译两传原文而略改动。这些都表明本书大部分出于编纂,而非翻译。本书所述传承出处,多无可考。”[ 田光烈:《付法藏因缘传》,见《中国佛教》(第4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118-119页。]
《景德传灯录》中对于二十八祖的具体叙述,多后世之公案话头风格,与印度佛教尚谨严议论之风迥异,显系佛教“中国化”后的历史重构,随举几例便见之,若:第三祖商那和修:
因问毱多曰:“汝年几耶?”答曰:“我年十七。”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师发已白,为发白耶?心白耶?”师曰:“我但发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景德传灯录》卷1 (CBETA, T51, no. 2076, p. 207, a8-12)]
第四祖优波毱多:
尊者问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来出家,非为身心。”尊者曰:“不为身心,复谁出家。”答曰:“夫出家者,无我我故。无我我故,即心不生灭。心不生灭,即是常道。诸佛亦常,心无形相,其体亦然。”[《景德传灯录》卷1 (CBETA, T51, no. 2076, p. 207, b29-c4)]
第六祖弥遮迦:
于阛阓间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问曰:“师何方而来,欲往何所?”师曰:“从自心来,欲往无处。”曰:“识我手中物否?”师曰:“此是触器,而负净者。”曰:“师还识我否?”师曰:“我即不识,识即非我。”[《景德传灯录》卷1 (CBETA, T51, no. 2076, p. 208, a19-22)]
第十祖胁尊者:
尊者问:“汝从何来?”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处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诸佛?”曰:“诸佛亦非尊者。”[《景德传灯录》卷1 (CBETA, T51, no. 2076, p. 209, a23-26)]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
有马鸣大士迎而作礼,因问曰:“我欲识佛,何者即是?”师曰:“汝欲识佛,不识者是。”曰:“佛既不识,焉知是乎?” 师曰:“既不识佛,焉知不是?”[《景德传灯录》卷1 (CBETA, T51, no. 2076, p. 209, b12-15)]
最有代表性的一条,恐怕是第十七祖僧伽难提的这段记述:
他时闻风吹殿铜铃声,尊者问师曰:“铃鸣耶?风鸣耶?”师曰:“非风非铃,我心鸣耳。”尊者曰:“心复谁乎?”师曰:“俱寂静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继吾道者,非子而谁。”[《景德传灯录》卷2 (CBETA, T51, no. 2076, p. 212, b20-24)]
“铃鸣”“风鸣”之论,与《六祖坛经》中惠能所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之说如出一辙,仿作之迹昭然。
事实上,《传灯录》将历代禅宗祖师之传承,编撰成昭穆分明、傍正次第井然有序的传法制度,并将之追溯至西土祖师,这显然并非欠缺历史时间观念的印度民族之风格,自应为注重宗法血缘、长幼有序的中华文化之典型特色。西天二十八祖谱系从唐代创制直至《景德传灯录》的最终定论,本身就是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之一重要表现。
二、关于七佛之偈
以七佛传心之偈作为禅史之开端,据现有之材料,应始于《祖堂集》而定型于《景德传灯录》,然《祖堂集》数百年未见于世,故以往学者多以始于《传灯录》者,若忽滑谷快天谓:“按禅门诸录,释迦佛以来有依一种特别之形式,授受禅的法门,展转传受至菩挺达磨。这禅门口诀,并非可为史的论究之事实。《景德传灯录》记道原于释迦佛前加上六佛成为七佛,列七佛所说之偈,以示从前佛有付法之偈。据宋契嵩《传法正宗记》卷一,则唐智炬于《宝林传》之首已有七佛之列名,然列七佛之偈者实从《景德传灯录》开始。”[ 【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6页。]——然《祖堂集》重现于世后,可见其中所载七佛之偈与《景德传灯录》基本一致,当即《灯录》之所本。《灯录》所载,更引据七佛传说之最初出处《长阿含经》之原文,以资取信,此为《祖堂集》之所无者。文谓:
古佛应世,绵历无穷,不可以周知而悉数也。故近谭贤劫,有千如来。暨于释迦,但纪七佛。案《长阿含经》云:“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冥。各各坐树下,于中成正觉。”又曼殊室利为七佛祖师。金华善慧大士登松山顶行道。感七佛引前,维摩接后。今之撰述,断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偈曰: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像。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
《长阿含经》云:“人寿八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剎利,姓拘利若,父盘头,母盘头婆提。居盘头婆提城,坐波波罗树下,说法三会。度人三十四万八千人。神足二:一名骞茶,二名提舍。侍者无忧,子方膺。”
尸弃佛。偈曰: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以下均有《长阿含经》之原文,兹从略。——笔者)
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
拘留孙佛。偈曰: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迦叶佛。偈曰: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
释迦牟尼佛,姓刹利。……说法住世四十九年。后告弟子摩诃迦叶:“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并敕阿难,副贰传化,无令断绝。而说偈言: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景德传灯录》卷1 (CBETA, T51, no. 2076, p. 204, c7-p. 205, c2)]
《景德传灯录》这段七佛之记述,忽滑谷快天有考证曰:“道原当录此等佛祖偈,先举《长阿含经》与关于傅翕之传说。《长阿含·游行经》有《七佛略传》,此仿释迦佛之传而作,痕迹昭昭,其记事千篇一律,可证成于一人之笔,苟为史而欲博信于后世者,绝不可依用如斯之传说。又傅翕非正传之禅者,其幻觉的事迹可作窥其思想之资料,却无力证明七佛之实在。道原不立脚于禅门正传之说,而举小乘经与他家梦幻的事实,非可以博信于后世。”[ 【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7页。]按:七佛之传说出于《长阿含·大本经》而非《游行经》,忽滑谷快天之论或有小误。——七佛之名,固出于早期印度佛典,然将之援入禅史并附以传心之偈,自当为后世之创作,忽滑谷快天查《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有《七佛各说偈》之经录,被视为疑经,并谓出自南朝齐世沙门道备,故疑其作者当为道备。[ 【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2页。]——其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就思想的考察而言,未必重要。七佛之偈语,表达的意思无外都是身心如幻如化,外境虚幻不实的大乘佛教“般若性空”之理。盖以不仅身体是假象,心灵也是假象;不仅恶是假象,善也是假象;不仅生是假象,灭也是假象;世俗所言的“佛”也好,“佛法”也好,在究极的佛教真理层面,无外全是虚幻的假名。《金刚经》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其中的道理,也就是释迦传法偈中所谓的“法本法无法”;反过来,“无法”也就是“法”,故谓“无法法亦法”。“无法”之境界,无形无相,所谓“说似一物即不中”。在禅宗看来,言诠文字,乃至三藏十二部经典,都不是真谛本身,只是促使众生开悟的方便手段。禅的境界,认为佛与众生本无差别,众生本来已具足佛性,只需唤醒内心深处的本真,便是开悟。——故七佛之偈者,盖以后世禅门之理以阐释印度早期佛教之传说,殆无疑问。
三、《景德传灯录》中尚无“拈花微笑”之传说
举凡关于禅宗“前史”中传法渊源的传说,应 “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最具文学色彩与象征意义,作为典故,亦多见于后世的诗文作品中。流风所及,乃至于当代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中,可谓人人耳熟能详。然成书于北宋的《景德传灯录》中尚无此说法,唯有“说法住世四十九年。后告弟子摩诃迦叶: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景德传灯录》卷1 (CBETA, T51, no. 2076, p. 205, b26-28)]云云之记载,更早的《祖堂集》之记载与之类似。至成书于天圣七年(1029)的李遵勗《天圣广灯录》中,始有“如来在灵山说法,诸天献华,世尊持华示众,迦叶微笑。世尊告众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嘱摩诃迦叶,流布将来,勿令断绝”[《天圣广灯录》卷2 (CBETA, X78, no. 1553, p. 428, c2-4 // Z 2B:8, p. 306, c1-3 // R135, p. 612, a1-3)]之说。——其最终定型之记载,则见诸成书淳熙十年(1183)的《联灯会要》,谓: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联灯会要》卷1 (CBETA, X79, no. 1557, p. 14, a6-8 // Z 2B:9, p. 220, d18-p. 221, a2 // R136, p. 440, b18-p. 441, a2)]
很可能《景德传灯录》的编者道原尚不知此一传说,或即使知道,亦未见采信。“拈花微笑”这则故事也从未见诸于禅宗灯录外的佛教经书,惟有《人天眼目》卷五引《宗门杂录》中说起王安石曾经见到出处,据云安石谓“余顷在翰苑,偶见《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三卷,因阅之,所载甚详。梵王至灵山,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舍身为床座,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登座,拈花示众,人天百万,悉皆罔措,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分付摩诃大迦叶。’此经多谈帝王事佛请问,所以秘藏,世无闻者”[《人天眼目》卷5 (CBETA, T48, no. 2006, p. 325, b8-15) ]云云。不过,这则记载本身出于耳食之言,未必可信。且《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世所不传,虽近代时曾于日本发现,但据考证,该经文字混乱,且未见藏经目录,应系伪经。忽滑谷快天谓该书“文义浅薄,非西土人之伪作,乃本邦人依《涅槃经》伪造,附会为台岭慈觉大师曾自大唐抄来”[ 【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72页。],或当出自日人手笔。——故就“拈花微笑”之故事而言,断为宋代中国人的创作,应无太大问题,其未见诸《景德传灯录》之记载,亦可视为“默证”。
这则传说将“拈花微笑”作为禅的高深意蕴,虽难以找到其印度佛教的思想渊源,却诚可与中国道家《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大音希声”之类认为大道难以用语言表述的理念相印证。《庄子·秋水》中更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对此郭象注云:“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儒门孔子,亦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之叹。毫无疑问,“不立文字”的说法与中国儒道哲学传统中的“得意忘言”之境可谓合若符节,自为“佛教中国化”之代表性产物。另从《传灯录》中尚无“拈花微笑”之说,而出于稍后之《联灯会要》这一情况看,亦略可推知禅宗前史之建构渐次生成之次第。
四、结 语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其后,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演化成中国化佛教。由于大小乘佛学同时传入中国,在其早期已经受到了汉代神仙方术、魏晋玄学思潮的涵化与影响,早期佛经翻译经过“格义”的阶段,亦使得佛学走向了贴近中国儒道哲学的诠释维度,逐渐形成独立于印度佛教而自成系统的汉传佛教宗派体系,唐宋以后席卷天下的禅宗,便是佛教中国化的最终产物。正如萧萐父先生曾指出的,禅宗思想之发生,乃为用中国哲学会通佛教教义,使之进一步中国化,从而构成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宗教哲学学派。故“禅宗思想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顶峰;同时,也就标志着中古哲学史上佛教这一整个思潮的发展‘圆圈’,达到了它的终点。这就是禅宗慧能学派所进行的佛教‘革新’运动的思想实质”。[ 萧萐父:《唐代禅宗慧能学派》,见《武汉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牟宗三则认为,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的佛性论之说,诚“不自觉地以中国儒家本有之骨格为背景,此所以谓之为中国心态之反映,谓之孟子灵魂之再现于佛家也”。[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1页。]麻天祥先生更认为禅宗本质上是“纯粹中国化的,又是大众化的庄老哲学”。[ 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2页。]故禅宗思想之发生,实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精神本质上的无痕换骨,以精微易简之中国文化智慧取代了繁密深邃的印度佛教思想,然就禅宗自身的传统而言,建立其合法性,仍自需追溯天竺之根源,此当即禅宗“前史”之传说建构之由来。这类历史现象,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之“被发明的传统”,他认为,“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因之“产生了需要由发明实践填补的空隙”。[ 【英】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航、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10页。]这类历史现象在中国也并不罕见,比如中国人自称“黄帝子孙”的说法,便很可能是晚清民初时才最终确立下来。禅宗将自身之历史谱系追溯至“西天二十八祖”乃至“七佛”,亦是如此。不过,若《景德传灯录》中这类“建构”历史之现象,虽未必全然为“事件的真实”,然其“意义的真实”则不容否认,其于文化认同之整合作用,亦自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作者通讯处: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武汉大学文理学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邮编:430072
电子邮箱:yn522664@163.com
电话: 18571640416
苏州工业园区重元寺出品
▍版权声明:
○ 本文部分文字为网络采集,由苏州重元寺编校发布,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
○ 版权归创作人所有,我们尊重著作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如涉及版权争议,请著作权人告知我方删除,谢谢。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苏(2022)05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