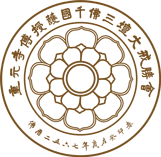{{year}}
摘要:《景德传灯录》自宋真宗敇准编入大藏经, 流行天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士人中引发了参禅之风的盛行,在僧人中也导致了融儒倾向不断深化,至明代发展到最高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大师向外大力宣扬儒、佛、道三教合一,及至清代出现了士人日益逃禅之风,佛学与儒学进一步趋向融合。
《景德传灯录》为宋代法眼宗禅僧道原所撰之禅宗灯史,原名《佛祖同参集》,集录自过去七佛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共一千七百零一人之传灯法系,对禅师的生平及重大事件均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全面反映了宋前禅家五宗之发展脉络。道原编成此书后,诣阙奉进,宋真宗命当时善于诗文的儒臣杨亿等人加以修定,并敇准编入大藏经, 遂流行天下。《景德传灯录》虽然颇多后世虚造之成分,然而,作为一部流传广泛的禅宗灯史,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史料及实用价值。故《景德传灯录》在宋、元、明各代流行极广,对文坛教界均有很大影响,“读《传灯》”几乎成为参禅的同义词。
一、《景德传灯录》发行的历史背景
唐末五代时期,佛教遭受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禁断,呈现衰微状态,直至宋朝始告再兴。宋太祖注重佛教文化建设,以重振佛教为太平兴国的政策之一,重视搜集散佚的佛典,尊礼高僧、建造译经院,曾于太祖乾德四年(966)遣僧人行勤等一百五十余人往赴吐蕃、印度等地,广求诸国佛法旧传及佛典,请回很多胡僧与佛籍。开宝四年(971)太祖再派高僧张从信往益州开雕大藏经。宋太宗时期,依然重视佛教文化,太平兴国五年(980),沙门知则进呈其所著《无量寿经疏》,宋太宗表示优礼,赐号“演教大师”。太平兴国七年(982),诏天息灾,施护等人于译经院翻译经论,遂形成宋初各代皇室重视佛教文化建设的祖宗成法。终宋一代,对佛教文化建设至为用心,尤其对沙门著书,多所优礼。
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宋代儒学复兴,史学及印刷术繁荣,佛教史学亦随之兴盛。宋朝历代皇帝执行太祖祖训,采取以文立国的国策,重文轻武,文人地位空前提高,儒学发展极盛,导致史学之繁荣,为佛教史学创作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而印刷术的应用,使得书籍文献得以广泛流传,使佛经印刷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在佛教方面,宋代以后,印度教典传译逐渐减少,中土佛学也逐渐由义理探研走向史料的编集与整理。古代寺院本为书籍荟萃之地,文化极盛之时,典藏必更富,僧人借此契机,大力促进宋代佛教史学的勃兴,刺激了宋代佛教史学的异常繁荣。前已述及皇家传统上就有对沙门著述多所优礼,或赐紫以示表彰,或将其书编入大藏以广流通,无疑大大刺激了僧人从事著述的热情。如《佛祖统纪》卷四三载:“端拱元年,翰林通慧大师赞宁上表进《高僧传》三十卷 。玺书褒美,令遍入大藏 。”【1】著述编入藏经,其书便可垂范后昆,传诸永久,故僧人每著书成,则上书皇帝以求将其书编入藏经。景德年间, 道原适应了学术发展之潮流,将禅宗历代祖师之言教汇编成《景德传灯录》一书,入京上进,真宗命儒士杨亿等人刊定,并下诏令编入大藏刊行,《传灯录》从此颁行天下。
二、《景德传灯录》与士人参禅之风的盛行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把佛教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笼络南方吴越等奉佛诸侯的主要措施。下令印刷大藏经,成立译经院,诏印度僧人和精通梵文的汉僧以及官僚士大夫组成译经集团进行译经活动,僧人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僧人开始趋向于士大夫化,与士大夫结友唱和。士人参禅问道也成为一种风尚,士人登祖师之堂者渐多。由于《景德传灯录》取材丰富,又为钦点,故终宋一代此书在士人之中广为流传。南宋楼钥《跋了斋<有门颂》帖》云:“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辈,只如学佛,或仅能涉猎《楞严》、《圆觉》、《净名》等经及《传灯录》,以资谈辩尔。”【2】可见《传灯录》已为宋人学佛参禅必读之书。
苏轼,又称东坡居士,与弟弟苏辙皆为宋代著名佛教居士,喜好参禅问道,与禅师多有往来【3】。苏轼初举进士时曾寓居太平兴国寺,三十年后再访兴国寺,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士人也曾寓居该寺,【4】苏轼《曹溪夜观<传灯录>灯花落一僧字上口占》云:“山堂夜岑寂,灯下看传灯。不觉灯花落, 荼毗一个僧。”【5】灯花落卷,烧一“僧”字,虽为打趣诗,苏轼夜读《传灯录》的情景却也跃然纸上。苏东坡的诗中往往“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6】足见苏诗采披之富,兼有佛学之素养,可见苏轼一生有着深厚的佛缘情结,《传灯录》更是苏轼的案头常备书。
苏轼弟弟苏辙信佛尤笃,辙为上蓝顺禅师弟子,上蓝顺为黄龙慧南之高弟。苏辙又与佛印了元、黄粟道全、绮州省聪皆有往来,与佛法因缘甚深。苏辙曾抄《传灯录》一卷,并作《书<传灯录)后》云:“去年冬,读《传灯录》,究观祖师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录之,置之坐隅。”【7】。苏辙《读<传灯录)示诸子一首》云:“大鼎知难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旧存古镜磨无力,近喜三更月到窗。早岁文章真自累,一生忧患信难双。从今父子俱清净,共说无生或似庞。”
《景德传灯录》为宋人参禅问道的必读书,是故宋人节录《传灯录》的也很多。赵抹与富弼皆为宋代著名之佛教外护与居士,赵抹曾书与富弼云:“近者旋附《节本<传灯>》三卷,当已通呈,今承制宋威去,余七轴上纳。”【8】赵林送富弼之书即为节抄的《景德传灯录》,由此可见节录《传灯录》并互相传抄是当时文人交流的常见方式。
南宋宋代临济宗高僧居简在《跋严太常编<传灯>》云:“太常丞严公,十八登科,官居余暇,取《传灯》千七百则佛祖机缘言句之切于日用者,搜英猎华,手抄巨编,老不释此书。易箦时,说四句褐遗子孙,一语不及家事,所成就者可知已。”【9】资料中严太常于为官公务之余,将《传灯》中适用于日常生活之佛祖机缘言句抄录成编,并以四句褐遗子孙,可见其佛学修为之深,抄读《传灯》已成为日常生活习惯。
《传灯录》成书之后,宋元明清历代均有刻印,影响很大。士人以或阅读、或摘抄、或题注等等形式参禅,蔚然风尚,延至清代竟至发生大批士人的逃禅之风。最为典型的当属屈大均。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成为普遍现象,屈大均“忽儒、忽释、忽游侠、忽从军” 【10】的特点,是岭南遗民中最典型的“逃禅”者,兼具遗民、僧人甚至学者的多重身份,心理呈现出矛盾的状态。这些士人血液里流淌着儒家的因子,表现出政治上的不屈服,然而面对现实却又无可奈何花落去,最终选择逃禅。佛教宗禅恰好符合了士大夫的这种精神需求,既能保有积极入世的态度,又能在失意之中求得心理慰藉。因此清代士人逃禅蔚然成风,尤其在岭南,对禅宗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三、《景德传灯录》与僧人融儒思想的演进
禅宗在印度佛教中本有一套修禅系统,但“只是印度佛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修行方式的一种,还没有形成一个具备完整的世界观、实践方法、认识论的教派体系”【11】。禅宗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魏晋文化相融合,历经唐代,“至宋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宋王朝力图糅合‘三教’,是顺应这种必然趋势,而且促使这种趋势更向前发展”,【12】佛教发展至宋代,禅宗五叶之云门、临济二宗兴盛,禅风也由以前的“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转变为阐扬禅机、谈玄说妙皆不离文字的“文字禅”,借助文字显示禅宗意境,强调“文以载道”。佛教由出世转向入世,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互相融汇、渗透,居士佛教大兴 ,禅师们与文人、士大夫交往十分密切,并在自觉不自觉中受他们影响。
禅宗大德在与士人的深入交往中,发现士人的诗句或富含哲理、或其所表达之境界与禅悟之境界极为相似,于是便在说禅论道中将这些诗句信手拈来,以警醒世人,表达神秘的悟道体验,暗示禅所追寻的“本心”。《景德传灯录》中不乏这样的例句:
问:“维摩与文殊对谈何事?”师曰:“唯有门前镜湖水,清风不改旧时波。”(卷十八“杭州西兴化度悟真大师”)此句源自贺知章《回乡偶书》中诗句,全诗云:“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禅师借用此句生动表达了“岁月变迁,而佛性不变”的禅机。
再有一例:
师领众出,见露柱。师合掌曰:“不审,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师曰:“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卷十一“杨州城东光孝院慧觉禅师”)师所咏句为杜荀鹤《子规诗》中之二句,全诗云:“楚天空阔月成轮,蜀魄声声似告人。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禅师接引学人每每苦口婆心,若学人愚钝不能悟,师家白费唇舌,而《子规诗》中此二句正可表达禅师的无奈。
禅师不仅在说教中引用士大夫的诗文,还在禅宗师资酬对中自创禅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曾有“禅机中有绝类诗句者”一条,引禅录中诗一百二、三十句,其中多数出现在《景德传灯录》中【13】,可见禅师的诗句创作颇具规模。在禅师的这些创作诗句中,往往兼具文学之生动意趣。如《传灯录》卷二十三“朗州大龙山智洪弘济大师”章:“问:‘如何是微妙?’师曰:‘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床边。’问:‘如何是极则处?’师曰:‘懊恼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前两句境界清明,解答了“微妙”之问。诗句由学人征问引出, 一问一答间甚是有趣。
宋代开始僧人儒融儒思想形成一种潮流,至明代发展到了最高峰。僧人对儒家思想的融合,已经从最初的援引及创作诗句深入到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上。明代四大高僧的出现就是典范,佛儒互渗达到了最高峰,其中又以憨山德清的融儒思想最为典型。憨山德清精通释、道、儒三家学说,主张三家思想的融合,对外大力宣扬儒、佛、道三教合一:“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14】并对《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做注,如《春秋左氏心法》、《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说》、《大学中庸直解指》等,完成了僧人从最初的借儒到最后融儒的转变。
四、余论
宋代《传灯录》的发行,加速了士大夫参禅之风的盛行,另一方面也促使僧侣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使得在士人与僧侣之间有了交流的可能。然而僧侣们结交权贵,以及频繁的诗歌创作等入世之行为,“皆为其欲达佛教中兴而不得不为者。”【15】明代中期佛教僧人过度倾向于宫廷交往,其后果必然导致一方面僧人因此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中,另一方面由于忙于世俗疏于自修,直接导致佛教僧才渐失,佛学日渐式微。直至明晚期,佛教有识之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转而以与儒学士人交往为传布策略,于是佛教从寺庙僧才教育改革开始,以四书五经融入僧才的教育与选拔,再次转向佛儒互渗的传布方向,僧人与士大夫互相凭藉对方之学,而提升本方之义理,万历时出现了诸如憨山大师这样通识儒学的僧才,佛学再次走向中兴。【16】佛儒互渗达到了最高峰,统治者及儒家士大夫更多地看到了佛教辅助王化的作用。宋真宗认为:“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17】宋孝宗制《原道论》对三教的功能与地位还作了明确的分工:“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18】朝廷对佛教的支持,除了选送僧人出去交流,还在国内大量刊发佛经,由此在士大夫之间广为传布;另一方面,佛教为了生存,也渐渐向儒学靠拢,更多地从出世走向入世,融合儒学的禅宗的出现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禅宗“不仅是佛教中国化发展历史的必然,是佛儒道三教融通的历史硕果,禅宗的出现还是中国宗教的成熟。”【19】佛教自身从理论到实践都越来越现实化,为国事祝福,为民生祈祷。
参考文献
【1】释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 49 册, 第 400页 。
【2】楼钥《攻娩集》卷七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景武英殿聚珍本。
【3】张 琪,苏东坡的佛缘【J】,佛学研究,2012,21
【4】梁建国,朝堂之外 :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9,02
【5】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
【6】《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首,四部丛刊初编本。
【7】苏辙《奕城集》第三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景明蜀府活字本。
【8】晓莹《罗湖野录》卷一“赵清献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宋)宋,居简《北碉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清)屈大均.屈大均集[ 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11】葛兆光.佛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7.
【12】杨渭生,两宋文化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页
【13】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五,四部丛刊初编本。
【14】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载《卍新续藏经》第 73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年,第 746 页;
【15】王启元,晚明僧侣的政治生活、世俗交游及其文学表现,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6】王启元,晚明僧侣的政治生活、世俗交游及其文学表现,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7】志磐:《佛祖统纪》,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第 405 页;
【18】志磐:《佛祖统纪》,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第 430 页。
【19】洪修平,韩凤鸣,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论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02)
(作者信息:黄雪晖,广东省韶关学院韶文化研究院;联系电话:18318331006)
苏州工业园区重元寺出品
▍版权声明:
○ 本文部分文字为网络采集,由苏州重元寺编校发布,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
○ 版权归创作人所有,我们尊重著作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如涉及版权争议,请著作权人告知我方删除,谢谢。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苏(2022)05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