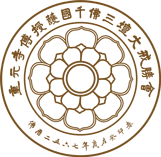{{year}}
【摘要】 在《景德传灯录》所记载的1701人中,有36人是居士,根据他们在《景德传灯录》中所展现主要形象及其对禅宗发展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功德,大概可以分为维摩型、修道型及护法型三种类型。与禅师群体相比,《传灯录》中36名居士的微弱之光,毫无疑问,会黯然失色,但实际上,恰恰是这些微弱之光,却折射出了禅宗的另外一种面相来:从弥勒菩萨的示现,到向居士的隐修、庞居士的活泼自在,再到帝王及地方藩镇等政治力量的护持,禅宗逐渐繁荣了起来,但这种繁荣几乎是以丧失禅宗的革新精神和独立发展空间为代价的。所以,鼎盛之际便是衰败之始。同时,从《传灯录》所记载的居士情况来看,不管是从最初的“东山法门”,还是到了晚唐时期相继出现的五个派系,其社会影响似乎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而并未真正走向平民化和世俗化。
【关键词】 《景德传灯录》;居士;生活化
《景德传灯录》,又称为《传灯录》,是北宋东吴高僧道原于景德元年(1004)所撰的一部禅宗史书,共三十卷,其中卷一、卷二记述了过去七佛、西天二十八祖的行化事迹等。卷三记述东土五祖,卷四记述了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的旁出法系。卷五记述了慧能法嗣。卷六至卷十三记述了慧能弟子南岳怀让的法嗣,包括沩仰宗和临济宗法系。卷十四至卷二十六记述了慧能弟子青原行思法系的法嗣,包括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法系。卷二十七记述了不在禅宗法系的其他禅门达者。卷二十八至卷三十记述了部分禅门高僧、大士、善知识的语录、赞颂诗文等。整体上来看,是书基本上体现了禅宗的形成及其在整个唐代的发展情况。全书共记禅宗传法世系52世,1701人。其中951人有机缘语句,其他有名无文。
姓名 | 是否有机缘语句 |
|
向居士 | 有 | 慧可大师法嗣 |
华闲居士 | 无 | 慧可大师法嗣 |
大士化公 | 无 | 慧可大师法嗣 |
和公廖居士 | 无 | 慧可大师法嗣 |
白松山刘主簿 | 无 | 弘忍大师法嗣 |
殷净 | 无 | 慧忠禅师法嗣 |
扬州总管李孝逸 | 无 | 慧安国师法嗣 |
工部尚书 张锡 | 无 | 慧安国师法嗣 |
国子祭酒 崔融 | 无 | 慧安国师法嗣 |
秘书监 贺知章 | 无 | 慧安国师法嗣 |
睦州刺史 康诜 | 无 | 慧安国师法嗣 |
晋州定陶丁居士 | 无 | 神秀禅师弟子普寂禅师法嗣 |
韶州刺史 韦据 | 无 | 慧能大师法嗣 |
义兴 孙菩萨 | 无 | 慧能大师法嗣 |
襄州居士 庞蕴 | 有 | 马祖道一法嗣 |
(庞蕴之女)灵照 | 有(附在庞居士章内) | 马祖道一法嗣 |
池州行者 甘贽 | 有 | 南泉普愿禅师禅师法嗣 |
宣州刺史 陆亘 | 有(除宋本外单独辟章记载外,其他版本均是将陆亘的机缘语句附在苏州西禅和尚章内) | 南泉普愿禅师禅师法嗣 |
杭州刺史 白居易 | 有 | 如满禅师法嗣 |
襄州常侍 王敬初 | 有 | 沩山灵佑禅师法嗣 |
幽州燕王(刘仁恭,《传灯录》中只言“幽州燕王”、“镇州赵王”,根据《释氏稽古略》卷第三“[唐昭宗]丁巳乾定四年(897)”:“……时真定帅王镕称赵王,庐王节度使刘仁恭称燕王,二王争相重敬”,(《大正藏》48/844c)所以此处的幽州燕王是指王镕、镇州赵王是指刘仁恭。) | 无 | 赵州从谂禅师法嗣 |
镇州赵王(王镕) | 无 | 赵州从谂禅师法嗣 |
(新罗)文圣大王 | 无 | 新罗大证禅师法嗣(怀让第四世) |
(新罗)宪安大王 | 无 | 新罗大证禅师法嗣(怀让第四世) |
(新罗)兴德大王 | 无 | 新罗洪直禅师法嗣 |
(新罗)宣康太子 | 无 | 新罗洪直禅师法嗣 |
相国 裴休 | 有 | 黄檗希运禅师法嗣(临济宗) |
睦州刺史 陈操 | 有 | 睦州陈尊宿法嗣(临济宗) |
唐肃宗皇帝 | 无 | 南阳慧忠国师法嗣 |
代宗皇帝 | 无 | 南阳慧忠国师法嗣 |
开封 孙知古 | 无 | 南阳慧忠国师法嗣 |
河南尹 李常 | 无 | 菏泽神会禅师法嗣 |
朗州刺史 李房翩 | 无 | 药山惟严和尚法嗣(青原行思第三世) |
澧州太守 雷满 | 无 | 澧州钦山文遂禅师法嗣(青原行思第六世) |
洪州南平王钟传 | 无 | 洪州上篮院令超禅师法嗣(青原行思第六世) |
善慧大士(傅大士) | 有 | 慧可大师法嗣 |
一、在《景德传灯录》所记载的1701人中,居士只有区区36人,有机缘语句者10人,但与成书于它之前的《祖堂集》中所记载的2位居士[
]来讲,已属难能可贵。为论述方便起见,兹将此36人按照原书的顺序,以表格形式予以列举(见表1)。
这36人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上至南朝梁(502-557),下至唐末洪州南平钟氏政权(882-906),前者如傅大士(497-569)为代表,后者以钟传(约847~906)为代表。几乎涵盖了禅宗的形成及其在整个隋唐时期的发展,但主要是集中在唐代。根据这36人在《传灯录》所展现主要形象及其对禅宗发展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功德(按:所参照资料不限于《传灯录》),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维摩型
维摩,即维摩诘,他是早期佛教的著名居士,据《维摩诘经》记载,他是从妙喜国土化生到娑婆世界,以居士相来化导众生。在《景德传灯录》所记载的有机缘语句的10位居士中,傅大士的形象和维摩诘的形象较为接近,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的居士姑且称为维摩型。根据《景德传灯录》记载:
善慧大士者,婺州义乌县人也。齐建武四年(497)丁丑五月八日降于双林乡父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监十一年(512),年十六,纳刘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会有天竺僧达磨(嵩头陀)曰:“我与汝毗婆尸佛所发誓。今兜率宫衣钵见在。何日当还。”因命临水观其影。见大上圆光宝盖。大士笑谓之曰:“炉鞴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足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彼乐乎?”嵩指松山顶曰:“此可栖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日常佣作,夜则行道……时有慧集法师闻法悟解,言我师弥勒应身耳,大士恐惑众遂呵之…… 异日帝(梁武帝)于寿光殿请大士讲《金刚经》,大士登座执拍板唱经成四十九颂……陈天嘉二年大士于松山顶繞连理树行道,感七佛相随,释迦引前维摩接后,唯释尊数顾共语,为我补处也……时有慧和法师不疾而终,嵩头陀于柯山灵岩寺入灭。大士悬知曰:“嵩公兜率待我。决不可久留也。”时四侧华木方当秀实欻然枯悴。太建元年(569)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众曰:“此身甚可厌恶众苦所集,须慎三业精勤六度,若坠地狱卒难得脱,常须忏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寝床,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钟来镇于此。”弟子问:“灭后形体若为?”曰:“山顶焚之”。又问:“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敛,但垒甓作坛移尸于上,屏风周绕绛纱覆之,上建浮图以弥勒像处其下。”又问:“诸佛涅槃时皆说功德,师之发迹可得闻乎?”曰:我从第四天来为度汝等,次补释迦,及傅普敏交殊,慧集观音,何昌阿难,同来赞助故。《大品经》云:有菩萨从兜率来,诸根猛利疾与般若相应,即吾身是也。”言讫趺坐而终,寿七十有三[ 《祖堂集》二十卷,五代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僧编。是书记述了自迦叶以至唐末、五代共二五六位禅宗祖师的主要事迹及问答语句。其中记载居士2人,即庞蕴和陆亘。]。
傅大士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佛教居士,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他降生、结庵嵩山、面见梁武帝、教导徒众、宣讲《金刚经》、创建双林寺,虽然是居士身,但其一生行化与法师无异,与达摩、志公齐称“梁代三大士”,开创了维摩禅。
2、修道型
修道型是指和禅师一样,进行实际的禅修,并有所成就的一类居士。在《景德传灯录》中形象生动,且有机缘语句者,如向居士、庞居士等。
向居士,北齐人,具体姓名现无从知晓,大约与禅宗东土二祖慧可同时,《传灯录》将其列入慧可大师门下,据载:
向居士,幽栖林野,木食涧饮。北齐天保初,闻二祖慧可盛化,乃致书通好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扬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大师命笔回示曰:“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礼觐,密承印记[ 【宋】释道原著,妙音、文雄点校《景德传灯录》卷三,成都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向居士的事迹,除《传灯录》外,最早附见于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中,在《传灯录》之后的《五灯全书》卷三、《居士分灯录》卷上、《居士传》十中。]。
根据以上记载,向居士大概是一个隐士,他远离喧嚣,“幽栖林野,木食涧饮”,这与傅大士结庵嵩山顶的情况有些相似,从中不难看出,早期禅门居士的隐修和苦行色彩。这种隐修和苦行有来自印度佛教本身的传统和惯性,但最主要还是受中国固有的隐士文化,特别是老庄思想的熏染。
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向居士在遇到慧可大师之前,对佛法已有一定的了悟,但这种了悟更多的是一种“天然外道”,正如明代朱时恩所言“向居士直捷见谛,暗合孙吴,然非二祖印证,不免天然外道。”[ 【明】朱时恩《居士分灯录》卷上,《卍续藏经》第147册]
庞蕴(生卒不详),字道玄,唐衡阳郡(今湖南省衡阳市)人。马祖道一禅师法嗣,《传灯录》卷八对其事迹有详细的记载,据载:
襄州居士庞蕴者,衡州衡阳县人也,字道玄,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唐贞元,初谒石头。乃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头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后与丹霞为友。一日,石头问曰:“子见老僧以来,日用事作么生?”士曰:“若问日用事,即无开口处。”乃呈偈曰:“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北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般柴。”头然之……后参马祖,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于言下顿领玄旨,乃留驻,参承二载。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乐头,共说无生话。”自尔机辩迅捷,诸方向之……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士曰:“某甲虽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秖如居士意作么生?”士以偈答曰:“无我复无人,作么有疏亲。劝君休历座,不似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主闻偈,欣然仰叹。居士所至之处,老宿多往复问酬,皆随机应响,非格量轨辙之可拘也。元和中,北游襄汉,随处而居。有女名灵照,常鬻竹漉篱以供朝夕……居士将入灭,令女灵照视日早晚及午以报。女遽报曰:“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居士出户观次, 灵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锋捷矣!于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问疾次,居士谓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公膝而化。遗命焚弃,江湖缁白伤悼,谓禅门居士即毗耶净名矣。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 【宋】释道原著,妙音、文雄点校《景德传灯录》卷三,成都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有关庞居士事迹,除《传灯录》外,《祖堂集》卷十五《庞居士传》、《人天眼目》、《五灯会元》卷三、《指月录》卷九〈庞蕴居〉士章、《居士分灯录》卷一、《佛教金汤编》卷九、《居士传》十七<庞居士>等中均有记载,但详略不一。]。
庞蕴,先儒后佛,在禅门颇具代表性,他参谒石头希迁、马祖道一,并在马祖道一处开悟,与禅僧问答酬唱,机辩明捷,是禅门行者悟道的重要典范和代表。特别是他和女儿灵照游戏自在的情节及全家习禅的描述成为戏曲、宝卷文学的重要题材。
3、护法型
护法型主要是指在禅宗发展有护持和传播之功的居士类型,当然护法型的居士也可以是修道型,但就其对禅宗的发展而言,其护持的功德和作用远大于其他方面,《传灯录》中所记载的这一类居士包括帝王与地方割据势力(如唐肃宗皇帝、代宗皇帝、幽州燕王、镇州赵王、洪州南平王钟传等),也包括政府官吏(如扬州总管李孝逸、工部尚书张锡、睦州刺史康诜、韶州刺史韦据、宣州刺史陆亘、襄州常侍王敬初、睦州刺史陈操、河南尹李常、朗州刺史李房翩、澧州太守雷满等),还有一些享誉士林的文人士大夫(如崔融、贺知章、白居易、贺知章、裴休等)。从数量上来看,这种类型的居士在《传灯录》中占大多数。
二、与禅师群体相比,《传灯录》中36名居士的微弱之光,毫无疑问,会黯然失色,但实际上恰恰是这些微弱之光,却折射出了禅宗的另外一种面相来。
从弥勒菩萨的示现,到向居士的隐修、庞居士的活泼自在,再到帝王、地方政权等政治力量的护持,禅宗逐渐繁荣起来,但这种繁荣几乎是以丧失禅宗的革新精神和独立发展空间为代价的。所以鼎盛之际便是衰败之始。
禅宗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体现,著名历史学家傅乐成先生在其名著《中国通史》中写道:
禅宗思想的光大,可以说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它是佛教从繁文缛节、繁琐的思辨和天竺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加以简化和中国化[傅乐成《中国通史》下册,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441页。]
这种中国化,既有教理教义方面,也有教团的组织和发展策略方面。孙昌武先生指出,一个宗派要想称为“宗派”,需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有依据佛教的基本教理、教义发展出的思想体系,有系统的“宗义”;二是有本宗派的教相判释方法;三是已构成“祖统”;四是形成本宗派独具特色的修持目标与方法;五是创建起构成宗派的僧团和宗派弘法基地的寺院,这些寺院又是有规模的经济实体[参阅孙昌武《禅宗十五讲》,中华书局,2016年8月第1版,第97-107页。]。所以,禅宗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宗派,是以道信禅师(580-651)、弘忍大师(601-674)黄梅僧团的创建和经营为标志,黄梅僧团无论是在修持主张与方法(“东山法门”),还是僧团的组织和发展策略上,都是以革新的姿态而面世的。
首先从僧团的发展策略和供给方式上来说,黄梅僧团一反南北朝时期佛教过分依附和服务于世俗统治的做法,而是继承“山林佛教”的精神,远离政治中心。
其次,从寺院经济的来源上来说,黄梅僧团一改南北时期僧团主要依赖外界供养的补给方式,而靠自力谋生,把农业生产劳作和修行结合了起来[孙昌武《禅宗十五讲》,中华书局,2016年8月第1版,第107页]。
第三,道信、弘忍作为僧团的领导者,一反南北朝义学拘泥经典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继承和发掘大乘心性思想,建设起简要精粹而又适应实践的新宗义,使严重偶像化、经院化、律仪化的佛教变成纯任自心,反对教条,张扬人性的新佛教[武则天虽于690年称帝,但由于高宗自660年10月起,风疾发作,头晕目眩,难以处理政事,所以大部分朝政委托时为皇后的武则天来处理,所以实际上她自660年10月起开始执政。于是让武则天处理朝政]。
这种新佛教在弘忍大师的弟子神秀大师(606-706)及其弟子普寂(651-739)、义福等人的努力下,冲出山林,名闻两京(长安、洛阳)。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660-705),[孙昌武《禅宗十五讲》,中华书局,2016年8月第1版,第166页]禅宗(北宗禅)的发展达到鼎盛,但这种鼎盛是以丧失“东山法门”的革新精神和僧团的独立发展为代价的,所以,鼎盛之际,便是衰败之始。僧团的整体生存和发展又回到了依附政治力量的窠臼里去了。所以,自此以后《传灯录》中所记载的居士大多是前文所说的护法型的了,譬如扬州总管李孝逸、工部尚书张锡、睦州刺史康诜等,这些都是地方或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而象具有隐修色彩的向居士这一类善信在《传灯录》中已难觅踪影了,即便是有,也是凤毛麟角。
三、在神秀及其弟子在两京积极弘法,为北宗禅的发展争取更大的支持的同时,慧能(638-713)所开创的南宗禅在神会(684-758)的努力下,由岭南逐渐走向中原。南宗禅在整体风格上“重新回归创造、革新的轨道”,在发展路线上几乎是“重复了北宗的路子”[孙昌武《禅宗十五讲》,中华书局,2016年8月第1版,第184页。]从宗义和修持方法上来看,
(南宗禅)把道信、弘忍的禅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提倡一种具有比北宗禅更丰厚的理性色彩和人本精神的、贯彻在人生践履中的禅。领悟这种禅,不需要隐遁出世、不需要凝神静坐,不需要严守戒律,也不需要阶渐修证……,禅是“无念”、“见性”的“顿悟”,是自我觉醒,是认识、肯定“自己”。这种禅作为佛教法门的一种,对于传统佛教教理与实践进一步全面革新[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1版,第125页。]。
南宗禅的这种革新精神为南禅宗的发展扫除了理念上的障碍,同时它打破了僧俗身份的局限,为南禅宗在摄授信众方面,奠定了理论上的优势。另外,由于其不拘泥于经典和宗教形式的限制,这一点南宗比北宗走的更远更彻底,也正是因为此,使得禅宗的精神迅速地渗透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了。它把修行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重新重视和肯定世俗生活,使人们不回避生活世界,在生活中完成内在性的超越,即“觉悟”,从而完成生命的蜕变,如庞居士所说的“神通妙用,担水劈柴”。如此一来,我们原本平凡无奇、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却显现出的它的神圣性,从而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义。信仰与生活也就完全统一了起来,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
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那样自我牺牲、苦修苦练,也可成佛。并且,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重要不只是“从凡入圣”,而更是“从圣入凡”,同平常人、日常生活表面完全一样,只是精神境界不同而已。“担水砍柴,莫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古尊宿语录》卷三)[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第404页]。
信仰与生活的统一的背后,实际上还是出世和入世的问题,佛教的中国化问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如何解决入世和出世的问题。就此而言,禅宗特别是南禅宗的出现,是一种突破,余英时先生认为:
唐代中国佛教的变化,从社会史的观点看,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从出世转向入世。慧能所创立的新禅宗在这一发展上尤其具有突破性或革命性的成就[参阅余英时<中国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
南禅宗的“突破性”或“革命性成就”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佛教的面貌,而且它所开启的新的宗教伦理对唐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孙昌武《禅宗十五讲》,中华书局,2016年8月第1版,第282页]。
安史之乱(755-763)之后,唐朝国力整体上呈现出衰势,在政治上朝廷对强藩的约束和控制已相当有限。就佛教所处的政治生态而言,代宗皇帝虽然崇佛,对佛教较为护持,《传灯录》也将其列为南阳慧忠国师的法嗣,但他主要是崇信密法,所以,禅宗在长安的生存空间已相当有限,所以,南禅宗的发展重心又重新回归山林,分散发展,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在八世纪末迎来发展高潮。出现了禅宗史上的所说的“五家七宗”,从宗义上来看,由于各个派系对禅解和禅修的侧重点不同,从而在接引后学的方式和语言上有所区别,即形成了不同的家风:
沩仰宗沉稳平实,深邃绵密,集中阐发“理事如如”、动辄合辙的宗旨;临济宗机锋峻烈,棒喝交驰,务使人截断常识情解而豁然开悟自家本来功夫;曹洞宗阐扬理事回护、圆融无碍观念,应机接物,言行相应,就语接人,富于思辨色彩;云门宗险峻简洁,往往在一言一句中见机趣;最后出的法眼宗具有综合性质,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顺机调物,气量平实,就禅思想的发展说,这些都无多新意[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2008年12月第1版117页。]。
所以,尽管在形式上和看禅宗似乎是在发展,但就其思想来说实际上并无太大突破,且渐趣僵硬化。加之,特别是唐以后禅宗各派系严守门风,互相诘难,客观上造成了禅宗的内耗。从发展策略来说,特别是到八世纪中叶以后,各大派系依持藩镇等地方势力为其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外在条件,如江西割据势力镇南节度使、洪州南平王钟传对云居道膺的礼遇和支持。裴休(791-864)在湖南观察使、潭州刺史任上时对沩山灵佑的护持,在江西观察使、洪州刺史任上对黄檗希运的礼遇和支持,成为沩仰宗和临济宗的成立的有力外护与保障。特别是临济宗在河北的发展、兴盛,离不开地方割据势力——成德镇的支持和保护。《传灯录》中提及幽州燕王王镕、镇州赵王刘仁恭都是赵州从谂的强力护法等。其他派系如云门、法眼等都是在地方割据势力的支持下发展、兴盛起来的。从派系的发展来说,这或许无可厚非,但就宗教的独立性而言,显然又走回了“教以辅政”的传统上去了,就此而言,北宗和南宗的命运又是何等的相似。
五、还是回到《传灯录》,从《传灯录》所记载的居士情况情况来看,不管是从最初的“东山法门“还是到了晚唐时期相继出现的五家,其社会影响似乎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而且禅宗对上流社会的吸引,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性的禅宗,这一点的突出表现就是唐以后文字禅的流行。
葛兆光先生在《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指出:
在四祖、五祖时代,一面用简捷方便的修习广开禅门,使禅法出现了生活化的走向,一面也用不断玄化的义理,是终极境界变得极为深邃玄远,只能靠深厚的文化素养与敏锐的内在心灵去体验,故而又有着明显的心灵化走向,这后一面则导致禅思想逐渐脱离了下层民众,而转向上层社会[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2008年12月第1版450页]。
可以说,禅宗的这种在宗义上的特点,当然更加容易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士大夫接受,而不是“愚夫愚妇”。所以,即便是在唐五代禅宗的发展的繁荣期,禅宗实际上也并“越来越平民化和世俗化,而是越来越贵族化和精英化了”。就此而言,禅宗远不如净土宗在社会一般的信众群体中的影响,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另外一点,尤为关键的是,禅宗所倡导的不拘泥于经典,不注重宗教形式的主张,是实际上对作为的宗教信仰的禅宗来说,恰恰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作为完整信仰体系而言,宗教的形式和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因为,对一般的信众来说,宗教形式实际上使其生发信仰、坚固信心、进行宗教体验的具体途径。没有宗教形式来呈现的宗教,很容易被作为文化而逐渐的被消解,这样作为信仰的宗教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在极力倡导佛教生活化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2】(南唐)静、筠二禅师《祖堂集》,中华书局,2008年2月第1版
【3】 (明)瞿汝稷《指月录》,巴蜀书社,2012年1月第1版
【4】(清)彭绍昇 撰,张培锋 校注《居士传》,中华书局,2014年6月第1版
【5】 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6】 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苏州工业园区重元寺出品
▍版权声明:
○ 本文部分文字为网络采集,由苏州重元寺编校发布,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
○ 版权归创作人所有,我们尊重著作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如涉及版权争议,请著作权人告知我方删除,谢谢。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苏(2022)0500009